| 书写习惯对数字空间表征SNARC效应的影响 |
2. 新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乌鲁木齐 830017
数字空间表征是人类对数字空间特性的表征,其中SNARC效应是数字空间表征的一个重要效应(沈模卫, 田瑛, 丁海杰, 2006)。SNARC效应也称“空间——数字的反应编码联合”效应(spatial-numerical association of response codes),最早由Dehaene等人发现于被试对数字1–9进行奇偶判断的实验,被试表现出对于小数1–4按左侧键快于按右侧键而对于大数6–9按右侧键快于按左侧键。研究者将这种现象用“心理数字线”来解释,即数字的相对大小是以一条从左至右从小至大的心理数字线形式编码储存,其大小与空间相对应,左侧表征小数而右侧表征大数(Dehaene, Bossini, & Giraux, 1993)。SNARC效应奇偶判断任务表明数字的大小与实验任务无关(Keus, Jenks, & Schwarz, 2005),当实验任务为屏幕中间呈现数字让被试对其数字的方向按左、右键反应时同样出现了SNARC效应,这说明该效应在数字大小信息与实验任务有关或无关的情况下都会产生(Fias, Lauwereyns, & Lammertyn, 2001)。
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发现SNARC效应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它不再局限于原有的狭义内涵,而是被广泛的用于描述“特定符号引发方向性空间偏向”(directional spatial bias)。如,研究者将实验材料替换为负数(Dodd, 2011)、英文字母(Jonas, Taylor, Hutton, Weiss, & Ward, 2011)或是汉语数字(刘超, 买晓琴, 傅小兰, 2004)均出现SNARC效应。同时研究者也发现SNARC效应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如Nuerk等人用两位数代替一位数作为实验材料,发现SNARC效应的产生会受实验任务的影响(Nuerk, Weger, & Willmes, 2001)。产生SNARC效应的方向也会因实验任务的不同而发生改变,当实验任务要求被试想象钟表上的数字时,SNARC效应产生了反转(Bächtold, Baumüller, & Brugger, 1998)。当改变注意条件时,阿拉伯数字及汉语数字的SNARC效应会因注意条件的改变而产生、减弱或消失(刘超等, 2004)。Bull在听觉障碍的被试身上发现了SNARC的反转效应(Bull, Marschark, & Blatto-Vallee, 2005);Ito采用日本人为被试(Ito & Hatta, 2004)、Schwardz通过眼动实验以眼跳潜伏期为指标(Schwarz & Keus, 2004)均发现了垂直方向的SNARC效应。我国学者对SNARC效应进行了一系列本土化研究,最早是发现了汉语数字同样存在SNARC效应(刘超等, 2004);继而又探讨了一位阿拉伯数字在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上的SNARC效应(沈模卫等, 2006);也有学者在汉语背景下验证了与SNARC效应相似的STEARC效应(spatial-temporal association of response codes effect)(顾艳艳, 张志杰, 2012)。
大多数学者支持SNARC效应的获得是由 “后天”文化因素以及读写习惯造成,而非遗传而来。Dehaene等(1993)的研究发现,读写习惯从右至左的伊朗被试移民到法国后,由于法语的读写习惯是从左至右,被试原有反转的SNARC效应强度随其移民时间的增长而降低,同时被试的标准SNARC效应强度增加。Rubinstan发现被试的年龄及数字技能水平对SNARC效应强度有影响(Rubinsten, Henik, Berger, & Shahar-Shalev, 2002)。Zebian选用阿拉伯单语者和阿拉伯-英语双语者为被试,研究发现阿拉伯单语者表现出反转的SNARC效应而双语者反转的SNARC效应较弱(Zebian, 2005)。定险峰等人通过实验证明SNARC效应是后天学习和经验的结果(定险峰, 靖桂芳, 徐成, 2010)。由于数字的空间表征具有情境依存性(张宇, 游旭群, 2012),我国学者发现在楼层情境与家谱情境下,SNARC效应在垂直空间维度上具有动态性(乔福强, 张恩涛, 陈功香, 2016)。
目前的研究多为汉语背景下的汉族被试,按照汉语从左到右的书写习惯使得汉语在水平轴上数字空间隐喻方向以从左至右为主,体现出来的SNARC效应就是被试按左侧键对小数的反应快于按右侧键对小数的反应,按右侧键对大数的反应快于按左侧键对大数的反应。本研究选取了维吾尔族作为被试,维吾尔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葛逻禄语支,其书写习惯是从右至左,但其对于阿拉伯数字的书写方向与汉族相同是从左至右,例如:“今天是2017年10月1日。”用维吾尔语则写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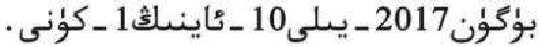 ”。这一书写习惯可能使维吾尔族的SNARC效应与汉族有所不同。本文选维吾尔族和汉族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并控制维吾尔族被试的汉语水平,以阿拉伯数字、维吾尔语数字和汉语数字为材料,采用数字大小判断任务,旨在探讨维、汉大学生水平方向SNARC效应的一致性、差异性及其影响因素。
”。这一书写习惯可能使维吾尔族的SNARC效应与汉族有所不同。本文选维吾尔族和汉族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并控制维吾尔族被试的汉语水平,以阿拉伯数字、维吾尔语数字和汉语数字为材料,采用数字大小判断任务,旨在探讨维、汉大学生水平方向SNARC效应的一致性、差异性及其影响因素。
探讨维、汉大学生阿拉伯数字SNARC效应的一致性。
2.2 研究方法 2.2.1 被试选取新疆师范大学在校汉族大学生21名(男生11名、女生10名);维吾尔族大学生21名(男生11名、女生10名),能熟练读写维吾尔语且MHK(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水平等级考试)未过三级。被试均为矫正视力正常、无色盲色弱、右利手。实验结束后可获得小礼品一份。
2.2.2 实验设计实验采用2(被试民族: 维吾尔族、汉族)×2(数字大小: 小数、大数)×2(反应手: 左手、右手)混合设计。因变量为被试反应时。
2.2.3 实验材料实验材料为阿拉伯数字。以5为分界,小数选1、2、3、4,大数选6、7、8、9。材料经Photoshop 7.0制作为黑色圆盘上的白色数字,黑色圆盘直径8 cm,白色数字直径6 cm,白色数字位于黑色圆盘中央;被试距离屏幕50 cm,视角为0.6°。采用华硕U303L笔记本电脑呈现实验材料,屏幕分辨率为 1024×768 像素,屏幕底色为灰色。
2.2.4 实验程序进入实验阶段,告知被试将要判断数字的大小,1、2、3、4为小数,6、7、8、9为大数。实验开始后(1)在屏幕中央呈现红色注视点300 ms;(2)呈现300 ms带黑色圆盘但无数字材料的空屏;(3)在黑色圆盘中呈现数字材料中的1个,并等待被试做出反应,在被试反应后进入下一组。实验为平衡设计,分为两个平衡部分,每部分刺激数字随机呈现,一部分被试在Block1中先左手按“F”键对小数反应,右手按“J”键对大数反应,在Block2中左手按“F”键对大数反应,右手按“J”键对小数反应;另一部分被试与之相反。每个刺激在单个Block中出现10次即在每部分出现20次,两部分共记录被试320次反应,两部分之间被试休息3分钟。在正式实验前有练习,被试错误率小于5%时进入正式实验。
2.3 结果与分析本实验统计数据分别为维、汉族被试从阿拉伯数字出现到被试按键反应的反应时,采用Spss23.0进行数据处理,剔除反应错误的数据与反应时超过平均值三个标准差的无效数据,剔除率为2.4%,得到反应时如表1所示。
| 表 1 维、汉被试对阿拉伯数字的反应时(ms)(M±SD) |
(1)对SNARC效应的分析
首先进行三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得到反应手与数字大小的交互作用显著,F(1, 20)=13.114,p<0.01,ηp2=0.23。民族、反应手、数字大小三者交互作用显著,F(1, 20)=10.162,p<0.01,ηp2=0.18。简单效应分析得到民族主效应显著,维吾尔族:F(1, 20)=8.921,p<0.01,ηp2=0.28;汉族:F(1, 20)=9.252,p<0.01,ηp2=0.21。其余主效应不显著。三因素交互作用显著说明民族对SNARC效应产生了影响。
对维吾尔族被试的反应时进行2(数字大小)×2(反应手)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被试反应手(F(1, 20)=1.371, p>0.05, ηp2<0.01)与数字(F(1, 20)=1.478, p>0.05, ηp2<0.01)主效应均不显著;交互作用显著,F(1, 20)=7.852,p<0.05,ηp2=0.41。简单效应分析得到大小数反应手主效应显著,小数:F(1, 20)=7.336,p<0.05,ηp2=0.31;大数:F(1, 20)=6.115,p<0.05,ηp2=0.26。维吾尔族被试对阿拉伯数字的小数判断出现左手反应时显著短于右手反应时,对大数判断出现右手反应时显著短于左手反应时,呈现正向SNARC效应。
对汉族被试的反应时进行2(数字大小)×2(反应手)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被试反应手(F(1, 20)=2.222, p>0.05, ηp2<0.01)与数字(F(1, 20)=0.719, p>0.05, ηp2<0.01)的主效应均不显著;交互作用显著,F(1, 20)=8.126,p<0.01,ηp2=0.39。简单效应分析得到大小数反应手主效应显著,小数:F(1, 20)=4.421,p<0.05,ηp2=0.32;大数:F(1, 20)=5.238,p<0.05,ηp2=0.30。汉族被试对阿拉伯数字的小数判断出现左手反应时显著短于右手反应时,对大数判断出现右手反应时显著短于左手反应时,呈现正向SNARC效应。
(2)进一步对左右手反应分析
对维、汉被试左手按键反应时进行2(民族)×2(数字大小)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被试民族主效应不显著F(1, 20)=0.572,p>0.05,ηp2<0.01;数字大小主效应显著F(1, 20)=13.288,p<0.01,ηp2=0.37;交互作用不显著F(1, 20)=2.264,p>0.05,ηp2<0.01。维、汉被试对阿拉伯数字左手按键反应时均表现出小数快于大数。
对维、汉被试右手按键反应时进行2(民族)×2(数字大小)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被试民族主效应不显著F(1, 20)=0.961,p>0.05,ηp2<0.01;数字大小主效应显著F(1, 20)=11.532,p<0.01,ηp2=0.42;交互作用不显著F(1, 20)=1.656,p>0.05,ηp2<0.01。维、汉被试对阿拉伯数字右手按键反应时均表现出大数快于小数。
3 实验二 维、汉大学生母语数字SNARC效应的研究 3.1 目的探讨维、汉大学生母语数字SNARC效应的差异性。
3.2 研究方法(1)被试 与实验一是同一批被试。
(2)实验设计 实验采用2(数字类型: 维吾尔语数字、汉语数字)×2(数字大小: 小数1–4、大数6–9)×2(反应手: 左手、右手)混合设计。因变量为被试反应时。
(3)实验材料 维吾尔文数字(小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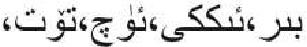 ; 大数:
; 大数:
)和汉语数字(小数: 一、二、三、四; 大数: 六、七、八、九),制作方法同实验一。
(4)实验程序 实验分两组,第一组为维吾尔族被试对维吾尔语数字进行反应,第二组为汉族被试对汉语数字进行反应。其余同实验一。
3.3 结果与分析本实验统计数据分别为维、汉被试从维吾尔语数字或汉语数字出现到被试按键反应的反应时,采用Spss23.0进行数据处理,剔除反应错误的数据与反应时超过平均值三个标准差的无效数据,剔除率为3.7%,得到反应时如表2所示。
| 表 2 维、汉族被试对维吾尔语与汉语数字的反应时ms(M±SD) |
(1)对SNARC效应的分析
进行三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得到民族主效应显著,F(1, 20)=32.711,p<0.01,ηp2=0.17。反应手与数字大小的交互作用显著,F(1, 20)=23.467,p<0.01,ηp2=0.25。民族、反应手、数字大小三者交互作用显著,F(1, 20)=19.535,p<0.01,ηp2=0.20。简单效应分析得到民族主效应显著,维吾尔族:F(1, 20)=12.884,p<0.01,ηp2=0.25;汉族:F(1, 20)=8.663,p<0.01,ηp2=0.27。其余主效应不显著。三因素交互作用显著说明民族对SNARC效应产生了影响。
对维吾尔族被试对维吾尔语数字的反应时进行2(数字大小)×2(反应手)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被试反应手(F(1, 20)=0.058, p>0.05, ηp2<0.01)与数字大小(F(1, 20)=2.271, p>0.05, ηp2<0.01)主效应均不显著;反应手与数字大小的交互作用显著F(1, 20)=8.905,p<0.01,ηp2=0.46。简单效应分析得到大小数反应手主效应显著,小数:F(1, 20)=6.115,p<0.05,ηp2=0.33;大数:F(1, 20)=6.718,p<0.05,ηp2=0.28。维吾尔族被试对维吾尔语数字的小数判断出现右手反应时显著短于左手反应时,对大数判断出现左手反应时显著短于右手反应时,呈现从右至左方向的SNARC效应。
对汉族被试对汉语数字的反应时进行2(数字大小)×2(反应手)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被试反应手(F(1, 20)=0.124, p>0.05, ηp2<0.01)与数字大小(F(1, 20)=0.003, p>0.05, ηp2=0.01)的主效应均不显著;反应手与数字大小的交互作用显著F(1, 20)=14.275,p<0.01,ηp2=0.38。简单效应分析得到大小数反应手主效应显著,小数:F(1, 20)=10.811,p<0.01,ηp2=0.27;大数:F(1, 20)=9.461,p<0.01,ηp2=0.29。汉族被试对汉语数字的小数判断出现左手反应时显著短于右手反应时,对大数判断出现右手反应时显著短于左手反应时,呈现从左至右方向的SNARC效应。
(2)进一步对左右手反应分析
对维、汉被试左手按键反应时进行2(民族)×2(数字大小)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被试民族主效应显著F(1, 20)=12.153,p<0.01,ηp2=0.40;数字大小主效应不显著F(1, 20)=1.175,p>0.05,ηp2>0.01;民族与数字大小交互作用显著F(1, 20)=21.472,p<0.01,ηp2=0.29,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左手按小数反应时汉族快于维吾尔族F(1, 20)=13.493,p<0.01,ηp2=0.24;左手按大数反应时维吾尔族快于汉族F(1, 20)=14.711,p<0.01,ηp2=0.21。
对维、汉被试右手按键反应时进行2(民族)×2(数字大小)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被试民族主效应显著F(1, 20)=10.791,p<0.01,ηp2=0.37;数字大小主效应不显著F(1, 20)=2.118,p>0.05,ηp2>0.01。民族与数字大小交互作用显著F(1, 20)=17.826,p<0.01,ηp2=0.27,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右手按小数反应时维吾尔族快于汉族F(1, 20)=10.694,p<0.01,ηp2=0.19;右手按大数反应时汉族快于维吾尔族F(1, 20)=9.887,p<0.01,ηp2=0.25。
综上,维吾尔族被试对母语数字出现从右至左方向的SNARC效应,汉族被试对母语数字出现从左至右方向的SNARC效应。维吾尔族被试对母语数字左手反应时小数慢于大数,右手反应时小数快于大数;汉族被试对母语数字左手反应时小数快于大数,右手反应时小数慢于大数。
4 讨论数字——空间反应编码联合(SNARC)效应为数字大小与空间对应存在联系提供有力证明,大部分学者用心理数字线来解释这种效应(Dehaene et al., 1993),认为数字按一定顺序映射到一条空间线段的不同位置上,即小数表征在左侧与左手相对应,大数表征在右侧与右手相对应,所以在对小数的反应左手快于右手而对大数的反应右手快于左手。在一些没有大小却有顺序的材料(如:英文字母)认知加工中也出现了SNARC效应(Gevers, Reynvoet, & Fias, 2003),这说明排列顺序对SNARC效应产生影响(王强强, 2015)。实验一比较了维、汉被试对于阿拉伯大、小数字的反应时,结果显示维、汉被试对阿拉伯数字均表现出从左至右方向的SNARC效应,表明维吾尔族在阿拉伯数字上的SNARC效应与汉族完全相同。这一结果验证了前人关于SNARC效应和心理数字线的假设,与Dehaene等人以及沈模卫等人的研究结果相同(Dehaene et al., 1993; 沈模卫等, 2006)。笔者进一步对维、汉被试的左手与右手进行分析,均得到左手反应时小数快于大数,右手反应时大数快于小数。这说明维、汉被试倾向于将阿拉伯数字的小数排列在左侧,所以左手对小数反应快;将阿拉伯数字的大数排列在右侧,所以右手对大数反应快。这可能是由于维吾尔族被试和汉族被试对阿拉伯数字的排序相同,均为从左至右,在对SNARC效应的方向上表现出一致性。
同时,数字被人们按其大小从左至右表征在心理数字线上(张丽, 陈雪梅, 王琦, 李红, 2012),而心理数字线假设是以书写习惯方向为从左至右的被试为基础,当被试换为书写习惯方向为从右到左的被试后其出现微弱甚至反转的SNARC效应(Shaki, Fischer, & Petrusic, 2009)。在实验二中维、汉被试对各自母语数字的SNARC效应方向呈相反结果。汉族被试由于母语数字与阿拉伯数字的书写方向一致,因此出现从左至右的SNARC效应;维吾尔族被试母语数字书写方向与阿拉伯数字相反,因此出现从右至左的SNARC效应。维吾尔族母语数字出现了与汉族母语数字相反的SNARC效应,产生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维吾尔语的书写习惯为从右至左,产生小数在右大数在左的空间对应关系,呈现从右至左的心理数字线。进一步对维、汉被试左右手反应时分析可以看出维吾尔族被试倾向于将维吾尔语大数排列在左侧而将小数排列在右侧,这与汉族被试恰巧相反,说明书写习惯不同的被试在对其数字的排列上具有差异性。所以说数字空间对应性与书写习惯是影响SNARC效应方向的重要因素。
5 结论本研究条件得出如下结论:(1)维、汉被试对于阿拉伯数字的SNARC效应存在一致性。(2)维、汉被试母语语言数字的SNARC效应存在差异性。(3)数字空间对应性与书写习惯是影响结果的重要因素。
定险峰, 靖桂芳, 徐成. (2010). SNARC效应起源的实验研究. 心理科学, 33(5): 1258-1261. |
顾艳艳, 张志杰. (2012). 汉语背景下左右走向的心理时间线. 心理科学, 35(4): 51-56. |
刘超, 买晓琴, 傅小兰. (2004). 不同注意条件下的空间-数字反应编码联合效应. 心理学报, 36(6): 671-680. |
乔福强, 张恩涛, 陈功香. (2016). 情境对序数的空间表征之影响. 心理科学, 39(3): 566-572. |
沈模卫, 田瑛, 丁海杰. (2006). 一位阿拉伯数字的空间表征. 心理科学, 29(2): 258-262. DOI:10.3969/j.issn.1671-6981.2006.02.001 |
王强强. (2015). SNARC效应的起因探究—大小还是顺序信息引起? (硕士学位论文). 东北师范大学.
|
张丽, 陈雪梅, 王琦, 李红. (2012). 身体形式和社会环境对SNARC效应的影响: 基于具身认知观的理解. 心理学报, 44(10): 1309-1317. |
张宇, 游旭群. (2012). 负数的空间表征引起的空间注意转移. 心理学报, 44(3): 285-294. |
Bächtold, D., Baumüller, M., & Brugger, P. (1998). Stimulus-response compatibility in representational space. Neuropsychologia, 36(8): 731-735. DOI:10.1016/S0028-3932(98)00002-5 |
Bull, R., Marschark, M., & Blatto-Vallee, G. (2005). SNARC hunting: Examining number representation in deaf students. Learning &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5(3): 223-236. |
Dehaene, S., Bossini, S., & Giraux, P. (1993). The mental representation of parity and number magnitud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22(3): 371-396. DOI:10.1037/0096-3445.122.3.371 |
Dodd, M. D. (2011). Negative numbers eliminate, but do not reverse, the attentional SNARC effect. Psychological Research, 75(1): 2-9. DOI:10.1007/s00426-010-0283-6 |
Fias, W., Lauwereyns, J., & Lammertyn, J. (2001). Irrelevant digits affect feature-based attention depending on the overlap of neural circuits. Cognitive Brain Research, 12(3): 415-423. DOI:10.1016/S0926-6410(01)00078-7 |
Gevers, W., Reynvoet, B., & Fias, W. (2003). The mental representation of ordinal sequences is spatially organized. Cognition, 87(3): B87-B95. DOI:10.1016/S0010-0277(02)00234-2 |
Ito, Y., & Hatta, T. (2004). Spatial structure of quantitative representation of numbers: Evidence from the SNARC effect. Memory & Cognition, 32(4): 662-673. |
Jonas, C. N., Taylor, A. J. G., Hutton, S., Weiss, P. H., & Ward, J. (2011). Visuo-spatial representations of the alphabet in synaesthetes and non-synaesthetes. Journal of Neuropsychology, 5(2): 302-322. DOI:10.1111/jnp.2011.5.issue-2 |
Keus, I. M., Jenks, K. M., & Schwarz, W. (2005). Psychophysiological evidence that the SNARC effect has its functional locus in a response selection stage. Cognitive Brain Research, 24(1): 48-56. DOI:10.1016/j.cogbrainres.2004.12.005 |
Nuerk, H. C., Weger, U., & Willmes, K. (2001). Decade breaks in the mental number line? Putting the tens and units back in different bins. Cognition, 82(1): B25-B33. DOI:10.1016/S0010-0277(01)00142-1 |
Rubinsten, O., Henik, A., Berger, A., & Shahar-Shalev, S. (2002).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l representations of magnitude and their association with Arabic numeral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81(1): 74-92. DOI:10.1006/jecp.2001.2645 |
Schwarz, W., & Keus, I. M. (2004). Moving the eyes along the mental number line: Comparing SNARC effects with saccadic and manual responses. Perception & Psychophysics, 66(4): 651-664. |
Shaki, S., Fischer, M. H., & Petrusic, W. M. (2009). Reading habits for both words and numbers contribute to the SNARC effect. Psychonomic Bulletin & Review, 16(2): 328-331. |
Zebian, S. (2005). Linkages between number concepts, spatial thinking, and directionality of writing: The SNARC effect and the reverse SNARC effect in English and Arabic monoliterates, Biliterates, and Illiterate Arabic speakers. Journal of Cognition & Culture, 5(1): 165-190. |
2.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Urumchi 830017, China
 2018, Vol. 16
2018, Vol. 16


